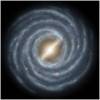往事并不如烟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782 篇文章
题图:孤独症孩子们在上艺术写生课。
作者:周静。今日二条是一土空间的夏令营介绍。
一诺写在前面:
今天文章的作者周静,有三个身份 — 孤独症(自闭症)孩子的妈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自闭症(孤独症)儿童救助基金主任、和北京BISS国际学校PTA的核心成员。
因为一土与 BISS 的合作,我认识了周静,她的女儿正在 BISS 上十年级,而大儿子是一名孤独症患者,从四岁确诊到如今二十几年,周静和先生一直陪着儿子坚持不懈地与孤独症抗争,完成了一场英雄母亲般的“自救”。今天的文章,就是她的故事。
年前周静和我提到,4 月 2 日是第十二个世界孤独症(自闭症)意识日,有没有可能在北京 BISS 国际学校举办第十二届“爱在蓝天下”艺术展及“和你一样”大型公益活动,让更多有爱的人们一起关注孤独症群体,我感到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现在很多地方推出了融合教育的指导意见,但是真正落地,还是有重重障碍,希望这些自下而上的推动,能带来一些切实的进步。活动是 3/31 号下午,我也会在。对外开放,报名在文后。
记得读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初见便感到书名起得好,后来细读文字,更觉得书名起得熨帖!虽是记录伤痛,文字却清新平缓。淡淡的忧伤在时光里摇曳,往事似要随烟波消散,但仔细聆听余音仍是袅袅。
喜欢章诒和不仅因为她的文字,更因为她敢于用笔去记录她的所见所感,即便那段记忆是那么的鲜血淋漓。钦佩之余也有感于自己,作为一个孤独症孩子的母亲,在这些年与儿子一起与孤独症抗争路上的心酸与洗礼。
许多人在听过我的故事后都会钦佩我所谓的勇气和决心,而对我来说,在这个我不能选择的境遇与命运里,我只不过做着一位母亲应该做的一切。
回看过去的 20 多年,从最初的茫然彷徨到后来的自救和与许许多多孤独症孩子父母的共救,与其说是我在帮助孩子们,倒不如说是孩子改变了我,让我从一个所谓“悲情故事”的主角变成了一个一诺常说的“乐天行动者”,直面现实,从我和身边的人与事做起,勇敢地去改变,甚至创造奇迹。
今天我可以说,我做到了,虽然前方的路依旧很长,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但只要出发,终于会有到达彼岸的那一天。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我的儿子于 1994 年 3 月 31 日出生在北京市妇产医院。剖腹产时间定在了 4 月 1 日。可那不是愚人节吗?!为了躲开这个日子,我跟护士长说我肚子疼,手术日期必须提前。主刀医生不得已临时加了台手术,就这样我儿的生日终于成功的避开了愚人节,但那时我们还浑然不知其实上帝的玩笑已经抛出了……
白白胖胖的他一到来便承载了我们所有的欢笑与希望。先生为儿子取乳名多多,我们就像其他所有初为父母的人一样,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很可爱。
▲ 一百天的多多。
他爱盯着看电视,当时电视台播放电视剧《年轮》,他喜欢听这剧里的主题歌,只要此剧开始播放歌声响起他会精力集中目不转睛的盯视。我们就用录像机录下来,一遍一遍给他播放。
他爱跑圈,在房间两头之间欢快的不断奔跑,经常浑身大汗淋漓也乐此不疲。
他的这些症状在他被确诊是孤独症(自闭症)后我们才知道这就是此障碍显著特征之一,而那时的我们却毫不知情。
第一个发现他出问题的人是我的母亲。记得那是我们带着不满两岁的多多一起给我母亲过生日,当大家一起唱完生日歌后,多多便开始如开启重复键一样连着十几分钟不停的在床上连跳带唱,兴奋的小脸通红满头大汗,我们则高兴的哈哈大笑。只有我母亲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
第二天一早母亲给我打来电话,委婉的建议我们带多多去看看医生。我对她的此举很不以为然,觉得我儿又能背诗还爱画画,认识各种品牌的汽车,怎么会有问题呢?!
多多的问题正式摆在我们面前是在他上幼儿园半个月后,园长找我先生沟通说怀疑这孩子是孤独症,让我们带他到医院检查。其实园长当时自己也不太懂孤独症,只是偶然看到过电视台播放一部讲述孤独症的专题片,觉得多多的很多表现与片中的孤独症男孩儿很像。
至此我们开始带着多多辗转于首儿、儿研所等著名儿科医院,遍寻名医后转到北大六院(国内最权威的孤独症专科诊疗医院),经专家最终确诊。
看到诊断报告上写着“疑似孤独症”的字样时,世界仿佛一瞬间在我眼前消失。没有悲伤、没有恐惧,因为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所有的意识已经在那一刻凝固。
▲ 被确诊一年后5岁的多多和爸爸,那时的他还很乖巧温和,爸爸则对几年后疯狂的多多毫无预判。
人在灾难面前开始都会惊慌失措,惊慌失措后是慌忙地应对。那时我和先生几近疯狂的搜寻所有跟孤独症有关的那一点点信息。有限的几本厚厚的医学书中包含关于孤独症的内容,篇幅却只有短短的一篇或半篇。我们逐条对照,不断地对自己说“他是!他不是!”
记得有一次先生出差,我自己在家反复阅读一段对孤独症大致描述的文字:孤独症属罕见病,发病率万分之一至万分之二,男女比例四比一,尚不知病因,没有任何生化介入手段,终身不可治愈。凝固的神经在那一刻突然恢复,痛苦如喷泉般从我的心底爆发出来。深夜时分的我完全不能自持:我的孩子没有了未来,我的生活陷入了死结……我想到了死。我给先生打电话,问他“我们怎么办?怎么办?”。
电话中他表现得很镇定,不断的安慰我。事后过了很久我才得知,那晚挂断电话先生一个人在酒店一夜未眠,因为他同样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崩溃后的我表现得近似疯狂。我开始遍寻民间“神医”。扎针、推拿、灌顶、求神问卜,外加口服各种“灵丹妙药”,让我儿尽尝百草。
记得 1998 年的冬天,在东四一间很冷的平房里,一个“神医”让多多浑身脱得精光,从头顶到脚面扎了无数根针。四岁的他站在一个火炉旁边,冻得嘴唇发青眼里透着惊恐。我看着心如刀割,但为了那一丝缥缈的希望残忍地配合着“神医”表演。“神医”针灸后又给开了七副中药,当场抓药交钱。一副药两百多元,每副药都要配金箔作为药引。明知含有重金属,但我俩依然狠心地逼着多多往下咽。恍如他咽下的不是苦药,而是一个家庭的未来,是我们无处找寻的希望。
这样的“求医”过程持续了一段时间,我耳朵如开着的雷达,搜寻扑捉着每一个“神方”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可以改变我儿的机会。此时的我智商指数降为零,大多数人都能一眼看穿的各种“骗术”,但我依然选择尝试。我的一位朋友实在不忍,善意的提醒我这样不对。我的回答是:“我无路可走,你能告诉我路在哪吗?”她走过来紧紧地抱着我,我则放声痛哭,那一刻我真是觉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们这群人未来的出路在哪,甚至没人知道还有我们这样一群人的存在。
经历了从绝望到疯狂再到绝望之后,我们反而开始平静,开始理性地接受眼前的一切,并变得更有韧性。我们准备开始自谋出路了。这是自立自强么?如果这是自立自强,那么大多数孤独症家庭都是这么过来的。
二十多年来,我所见到的所有孤独症家庭,自孩子被诊断为孤独症时起,整个家庭便开始永无安宁之日。拉着孩子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历经磨难。我常笑谈,我们这些孤独症孩子的父母特别像取经的唐憎,我们的孩子就是取经路上的妖怪,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时时刻刻变换着方式来考验你,磨炼你的耐心,考验你的爱心。
原本我以为只有我的家庭这样,直到通过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认识了更多的孤独症家庭以后我才发现,大家都经历着同样的辛路历程。
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是中国第一位孤独症医学专家杨晓玲大夫。杨大夫 1986 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开设了孤独症医学专科门诊,也是在这一年诊断出中国第一例孤独症患者王巍,这个当年的孩子今年也已经 51 岁了。
当时孤独症一词还不被世界熟知,据当时文献记载该病症全球发病率为万分之一,属罕见病。国内对此病症更是知之甚少。
我国第一批被诊断出的孩子现在都已是 30 多岁的中青年。当年杨大夫本着医者仁者的人文情怀带着她的学生贾美香大夫等人与我们这些无助的家长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孤独症救助民间社团,联手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走上了孤独症孩子与家长的自救之路,我和先生也加入了这个社团,开始了自救与救他之路。
一场孤独症孩子家长的自救和共救
还记得协会成立之初,每次会议家长们都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颇具“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之感。往往是一位妈妈上台发言,开口没说两句便哭着跑下台。那时的我们不敢想也来不及想孩子的未来,摆在眼前的幼儿园、学校等一道道关都很难逾越。
随着加入协会的孤独症家庭越来越多,老家长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新家长的“知心姐姐”。虽然依旧前途未卜,但好在可以抱团取暖,在心境上不再那么绝望孤单。此时,杨大夫等专家也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开始跟我们家长一起奔走于卫生部、市政府等政府部门之间。
各部门接待人员在听到“孤独症”三个字后的第一反应都是“孩子不说话吧?你们家长是不是太忙而没时间管孩子?是养育方法不得当吧?”我们一遍一遍的解释“孤独症是一种病症,是先天性的生理问题,目前是世界医学界的难题,没有破解,我们需要帮助。”接待人员也是一脸的为难,他也不知该如何处置,只是说我们向上反映。
既然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我们开展讲座培训,举办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等各种途径发声,呼吁社会关注到孤独症这个特殊群体,使公众了解这个群体面临的困境,也恳请政府出台政策,拯救这个群体于苦海。多年的持续努力终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 2008 年 4 月 2 日世界第一个孤独症日起,由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主办,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一届“爱在蓝天下”孤独症儿童画展,超过 1000 多名孤独症孩子展出了出自他们的上万幅作品,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顾秀莲、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志珍、民政部原副部长刘光和、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等领导都曾亲临画展现场看望孤独症孩子,了解孤独症人群。
▲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顾秀莲来画展现场看望孤独症孩子们。
▲ 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来画展现场看望孤独症孩子们。
2015 年 7 月 19 日,协会还在米兰世博会的中国馆举办了“爱在蓝天下”中国馆主体日展览及“无语言的交流”公益活动。
在 2016 年、2017 年,协会还分别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来自星星的艺术”和“来自中国美术馆的温度”两届画展。我们希望通过画展、文艺演出等公益活动,将孤独症人士积极阳光的一面展现在公众面前,使他们能够收获一份作为一个自然人应有的尊严。
同时世界各国对孤独症的整体认识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各种康复训练手段层出不穷。仿佛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一组数据却让全世界为之震惊。
据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人口普查结果统计,从 2010 年至今孤独症的发病率极速上升,美国每年对全美 3 岁至 17 岁的人群做普查,2018 年公布的统计数据现实,孤独症的发病率为 1/59,发病率已接近 2%。
我国尚未开展全面统计,北大六院曾在北京城四区做过儿童孤独症早期筛查,结果为千分之六。去年卫计委公布预估我国新生儿孤独症发病率是 1%。这就意味着更多的多多们会出现在我们身边……
更为可怕的是,即便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孤独症仍然不可治愈。这已不再是只涉及一个小众群体的罕见病,孤独症已经开始关乎整个人类的未来。
孤独症康复事业任重而道远,即便已发展二十余年的协会也颇感力不从心。2011 年,我们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下发起成立专项基金。我的身份也由一名普通孤独症家长转变为全职从事孤独症康复事业的公益从业人员。我笑谈我此生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度我!而我也因生命中的他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 母亲节多多在老师的辅导下将他的作品《妈妈》送给了我。
换一个角度看公益
从一个接受帮助的受助者到一个给予帮助的施予者,我不得不重新看待公益的介入手段。纵观当下国内的诸多的品牌公益项目,大都在卖惨晒可怜。是啊,不惨不可怜又有谁会来帮助你呢!可我不能在没有得到我儿子的授权的前提下靠卖惨去博取公众的同情,我也更不想丢掉我作为一个母亲最后一点尊严用揭开我孩子伤疤的方式换取外界的同情。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能与人言无一二。每个人光鲜的背后不都有不为人知的苦楚?!在与团队协商之后决定我们可以流汗绝不流泪,我们也想试试闯出一条新型的公益之路,站着去为孤独症们争取一个有尊严被尊重的社会环境。
协会里一位家长是清华美院李睦教授,他本人也是画家。他发现他儿子李昂的涂鸦很有特点,笔触及风格有着特有的本真,画面也会随着他的情绪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他跟别的家长联系,让家长把孩子涂鸦的作品发给他,发现有些孤独症孩子们的作品有着常人不具有的特质。
2011 年协会的一位家长林捷帮忙协调资源联系了林依轮、那英、王中磊等众多明星组织慈善活动筹措善款支持我们在 798 艺术区成立了“天真者的绘画”工作室,由此我们设立了“星光益彩”孤独症人士艺术疗育公益项目,通过美术、音乐、器乐、舞蹈,等等,艺术手段介入,结合科学的康复训练方法,来对孤独症人士进行康复训练。
▲ 摄于2018年世界孤独症日公益展演。
过去 7 年多,“天真者的绘画”工作室分别为孤独症孩子开设了绘画、手工、花艺、音乐、打击乐、舞蹈、烘焙、保洁家务劳动、游泳、篮球、足球等多门课程,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下帮助他们提升听从、模仿、跟随、轮流、手工操作、团队协作等各项基本能力,这样更有助于舒缓他们的不良情绪,培养生存所需的能力,增进他们的康复疗育进程。
<< 滑动查看下一张图片 >>
▲ 在上课的孤独症孩子们。
▲ 作者和团队一起为孤独症孩子开设的森林疗愈课。
让更多孤独症人士能“老有所养”
孤独症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不同,他们终身没有独立的能力,需要被照顾。但随着父母年龄老去,我们最大的担心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像多多这样大龄的孤独症的孩子们又该如何面对这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
记得在十多年前,一位孤独症孩子父亲 F 老师就曾经在在众人面前戏言:
我走时必须带上儿子,不能让他自己留在世上。
事实上,今天面临艰难抉择的,除了 F 老师,还有许许多多正在步入暮年的孤独症父母们。但当下社会对这群有可能在中年以后失去父母的孤独症孩子的帮助却依然少之又少。
北京一家精神病医院自从收了一个大龄孤独症患者后,因这个孩子的躁动与难以交流,从此他们就再也不收孤独症孩子了。
心凉如水,悲情如潮,不禁也想起 F 老师的戏言,“我一定会带他走的,不让他自己留下来!”这话其实是对孩子最好的结局,只是父母中的一人要行事果决断然,否则父母就不能瞑目了。
有关机构曾做过小范围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精神残疾人士父母双双故去后离开家庭居住在福利机构以后,平均生存时间只有 1 年。各种原因无须言表,但精神残疾人士的自身生存及生活自理能力低下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 在2017年世界孤独症日的活动现场,我们发布了视频短片《我的梦想》,讲述了几位大龄孤独症患者及其家长代表的真实生活状况,令当时与会的诸位政府领导,以及数百位现场嘉宾数度为之落泪。
严峻的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战略调整。自 2017 年开始逐渐将工作重心向帮扶大龄孤独症人士倾斜,希望通过公益手段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公众关注大龄孤独症群体,并携手为其探索一条通往未来的生存之路。
2018 年世界孤独症日的活动现场,我们联合国内孤独症相关领域多家权威单位共同宣布筹建工作委员会,通过工作委员会让全国各级各类孤独症机构在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交流,促进孤独症的早期筛查、早期干预、康复训练、特殊教育、融合教育、学术研究等方面工作的发展,规范孤独症的康复与教育,尤其要填补大龄孤独症领域服务空白,切实推动中国孤独症康复事业积极健康发展。
2019 年世界孤独症日即将来临,我们将会正式向社会发布“星翼计划”公益项目,为大龄孤独症人群提供社会性生存能力的培养课程,提升自闭症患者生活品质,延长他们的生命周期。
同时,有感于多位大龄孤独症孩子家长对于今生无缘见证儿女的婚礼、无法实现牵着孩子的手走上红毯的遗憾,我们想在今年的活动内容增加成人礼仪式部分,圆大龄孤独症家长们此生心中的夙愿,慰藉他们多年来的艰辛。
欢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机构与我们携手,加入“星翼计划”,为中国孤独症的康复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相信天助自助者!救赎是需要施救者与被救助者共同发力。我们这些孩子们用他们点滴的进步回馈着所有给予他们帮助的爱心人们!
回想起我儿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磨难,我的好友经常说“你俩太不容易了,这要换成是我真是不知该怎么办?”有时多多情绪失控发狂,家里如同灾难片的片场,我也会发狂崩溃。我抱着女儿痛哭,说对不起她,不该生她,不该把她带到这个家庭而受难。女儿说她不觉得是受难,她觉得这个家很幸福,哥哥很可怜,我们应该厚待他。
是啊!当我看到长大的女儿外出拉着哥哥的手,吃饭时给哥哥夹菜嘴里说着“哈多,吃吧”。我则翻眼看着她“这是你哥,凭什么叫我们哈多,你才哈呢。”女儿则哈哈大笑,我儿也高兴地咧嘴嘿嘿的笑了。
▲ 妹妹来了,多多用歇斯底里的折腾向我们宣誓不能因为妹妹的到来而剥夺我们对他的关爱。
这就是生活吧,不好中总有好的一面,我们哭着、笑着、混着、熬着,有太多不如意,也有太多的纠结与挣扎,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
希望你也能加入我们,就像我们画展十多年不变的主题“爱在蓝天下”,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和呵护与尊重。
为迎接第十二个世界孤独症日(自闭症)的到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及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携手一土教育及北京 BISS 国际学校,共同举办“和你一样”大型公益活动。
现场将举办画展及演出,为孤独症孩子奉献爱心,并共同呼吁社会对于孤独症人士的关注,主要内容包括:
“爱在蓝天下”孤独症孩子绘画作品及高中学生艺术作品展示和义卖
中国自闭症领域专家贾美香大夫带来倾情讲述
爱心公益明星李小萌、陈碧舸、钢琴家印芝、舞蹈家张雪峰莅临演出
孤独症孩子与一土、BISS 学校的低年级孩子的合唱表演
BISS 高年级学生将带来原创钢琴曲、男声合唱,并与孤独症孩子四手联弹
见证大龄孤独症孩子与各校高年级学生共同带来的成人礼
正式发布大龄孤独症患者救助项目“星翼计划”
活动时间:2019 年 3 月 31 日,下午 2 点至 5 点
活动地点:北京 BISS 国际学校(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四区十七号楼)
本次活动免费,面向所有支持参与公益活动的学龄阶段孩子及家长开放。你不需要是孤独症家庭,如果希望带孩子参加一个真实的公益活动,了解和支持这个群体,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一起。请长按识别以下二维码填写报名表,活动主办方将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通过邮件与您联系确认报名(请务必确保邮件地址填写完整正确)我当天也会在,希望能见到你们。
活动当天请持有效的身份信息到场,核验后方可入场。谢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 END -
推荐阅读
你读到的只是冰山一角,看经典热文,点击菜单。
有感悟想和大家分享,
请给邮箱 nlsh88@163.com 投稿吧。
欢迎转发分享;对话框输入“转载”即可了解授权详情;未经授权,不得用于微信外的平台。
1、头条易读遵循行业规范,任何转载的稿件都会明确标注作者和来源;
2、本文内容来自“奴隶社会”微信公众号,文章版权归奴隶社会公众号所有。